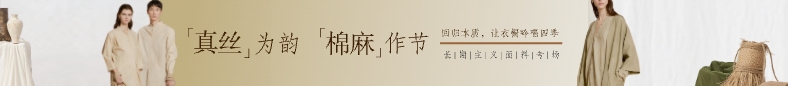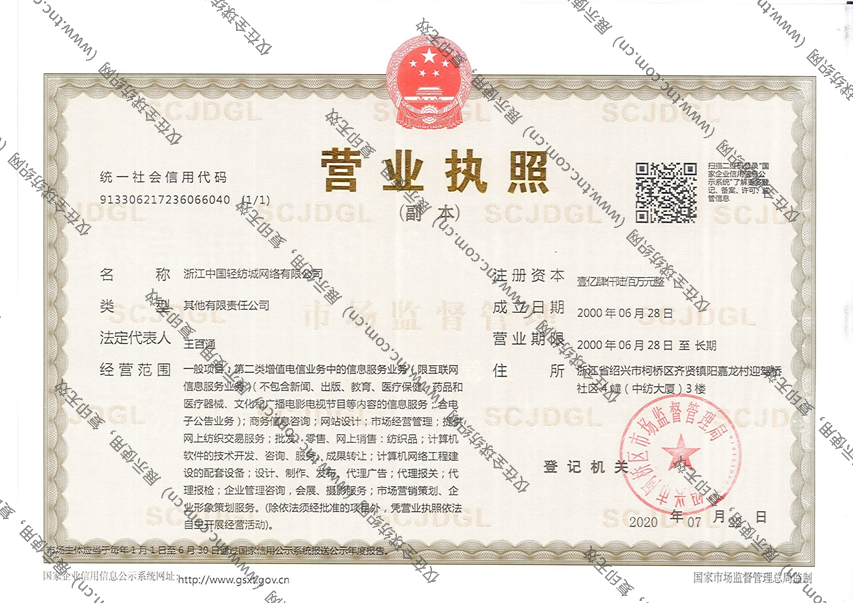北宋青白釉雕瓷“佛獅戲球”瓷枕。
人類發明工具總是在彌補先天上的不足,用錘子彌補拳頭,用輪子彌補腿腳,用刀子彌補爪牙,用文字彌補記憶……然而野生動物似乎從來不用枕頭,人類為什么會有這樣普遍的剛性需求,以致幾乎所有的文明都發明了枕頭——這暗示著我們有什么先天不足嗎?
應該說,枕頭的發明正是直立行走留下的后遺癥。雖然陸生脊椎動物不乏二足行走者,比如鳥類和袋鼠,但是它們后肢的支點都在身體重心附近,軀干在運動時仍然平行于地面,人類的后肢卻完全長在軀干末端,為了直立行走就不得不讓脊柱完全垂直于地面,胸腔因此完全打開而變得扁平。
鴕鳥、袋鼠和人類的骨骼對比:鳥類的髖關節前移接近身體中部,并有大型的尾羽平衡重量,頸部呈現s型保持軀干水平;袋鼠用粗大的尾巴平衡身體的重量;人類沒有這些措施,將全部體重經由脊柱垂直傳遞給大腿骨。
同時,人類雙手具有復雜的功能,包括投擲、揮舞、探取等大幅度動作,這要求人的肩關節必須足夠靈活,在其它哺乳動物身上平行于軀干兩側的肩胛骨因此變得寬而短,平鋪在了后背上;在其它哺乳動物身上短小甚至消失的鎖骨也變得結實修長——這讓人類有了一對格外寬闊的肩膀,軀干因此更加扁平。
這些都對人的睡姿產生了影響:失去了前肢的支撐,像其它哺乳動物那樣趴著睡就會壓迫胸腔難以呼吸;仰臥會拉伸脊柱的生理彎曲,讓背部緊張,四肢也不能自由擺放;哺乳動物最放松的側臥姿態又會讓頭部懸空,久之令頸部肌肉疲憊不堪,引發急性纖維組織炎癥(落枕)。所以綜合起來,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頭部墊到合適的高度側著睡,這就是發明枕頭最主要的原因——但不是全部原因。
枕頭的發明與人體結構有關,枕頭讓睡眠更舒適。
另一個原因是人的體型夠大,自身重量和血液重量都能產生可觀的宏觀影響。
我們可能注意過,貓幾乎可以在任何坎坷的地方睡著,而人睡覺的時候床單上有一個褶子都會咯得不舒服。這是因為體重越小的動物相對表面積越大,躺下來的時候下方組織壓強越小,貓這樣輕盈的動物已經無法理解“硌”的含義。
但人體足夠沉重,可以給受力組織相當大的壓強,當支撐面不夠平坦時就會發生應力不均,身體內部的骨骼也會向下壓迫周圍組織,這都會在局部產生強烈的觸感和疲勞,長期臥床的病患甚至常常因此發生褥瘡和血栓,所以人睡覺總會不自主地翻身。既然人的胸腔格外扁平,肩膀格外寬闊,也就格外需要一個枕頭在翻身時穩定頭部。
不僅如此,人的血液更多,也更沉重,當人躺在平面上的時候,頭部總是比軀干更低一些,這就會讓頭部血壓明顯升高,睡久了昏昏沉沉不舒服,有些胃病患者還會遭遇胃酸倒流的情況,所以僅僅為了舒服,人也愿意將頭墊高一些睡。
當然,也并非只有人類有枕枕頭的需求,我們的大型靈長類近親同樣面臨著胸腔扁平而身體沉重的問題,比如大猩猩就有三種常見的睡姿:仰臥,隨便枕個什么東西或者把雙手抱在后腦勺;側臥,枕著手睡;趴著睡。而對于更加聰明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,他們懂得用枝葉搭一張床,給腦袋一個合適的位置,功能就相當于枕頭。
最后,靈長動物之外的大型哺乳動物,特別是食草動物,往往趴著睡,這樣可以及時站起來奔跑,如果環境允許,它們也絕不錯過側躺放平或者找東西枕著的機會。但是最大型的象類由于體重過大,胸腔無法在躺下時支撐重量,所以只能站著睡。